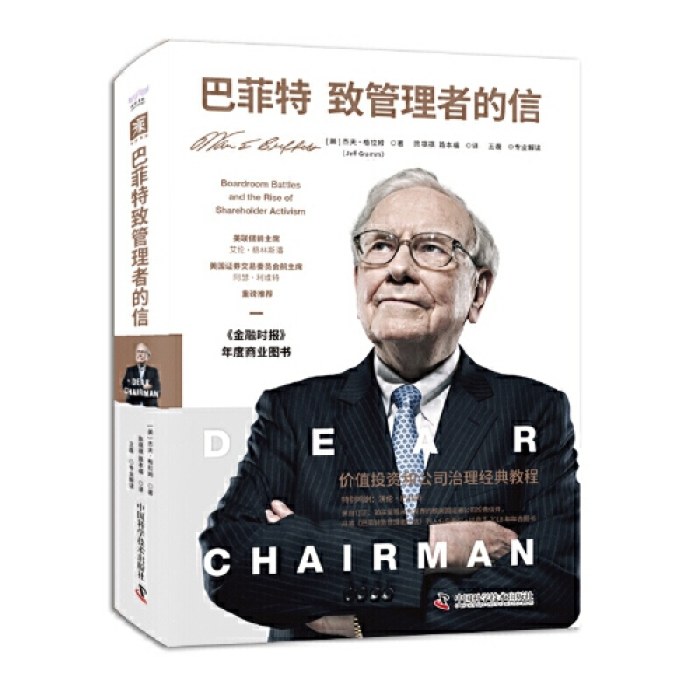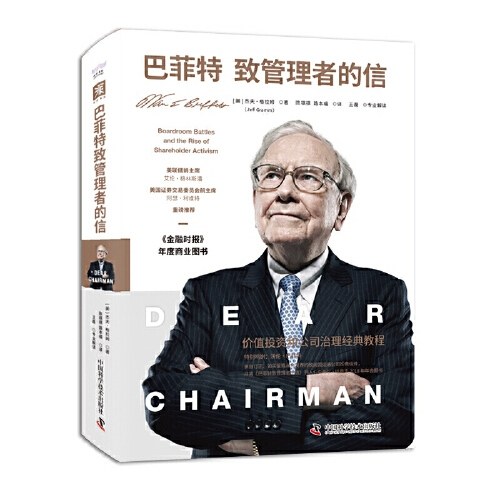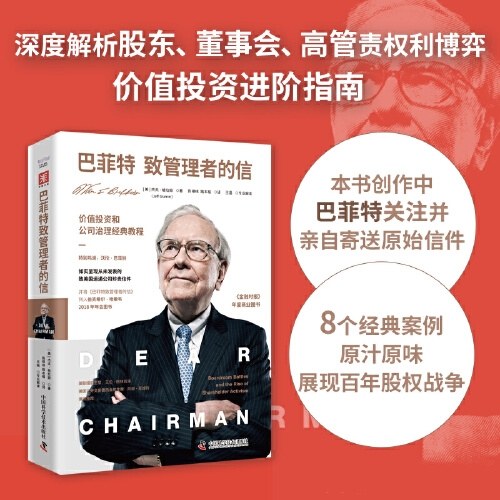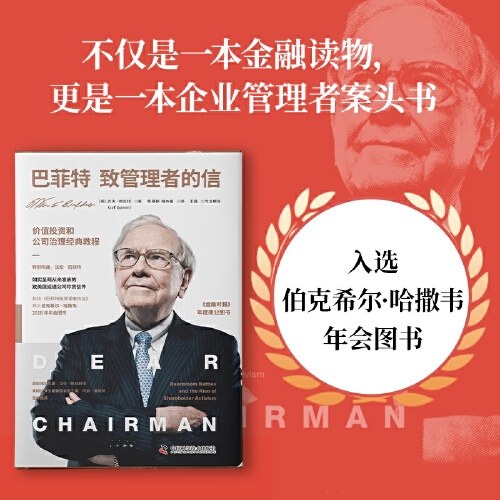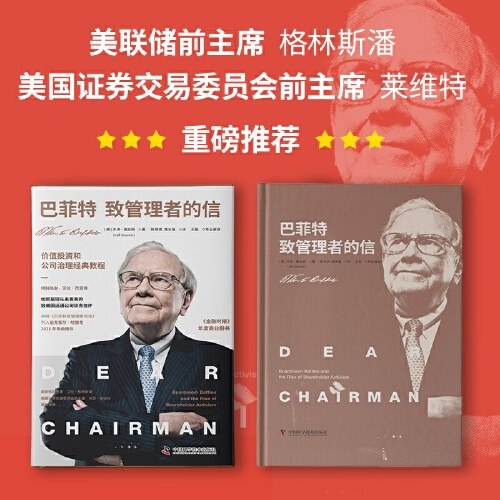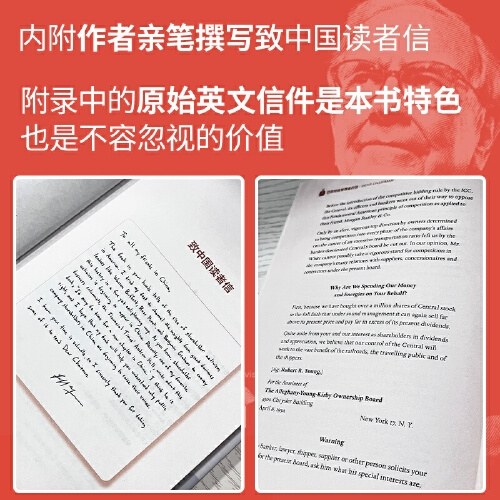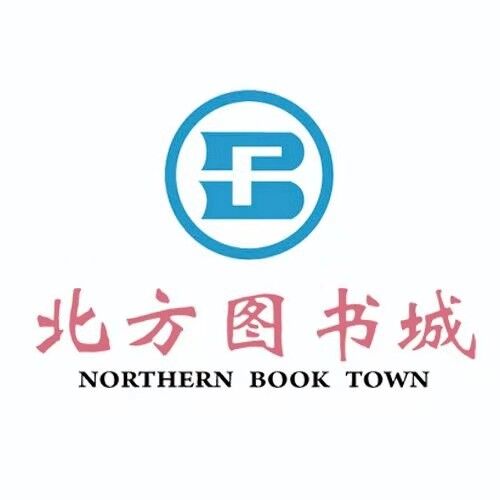看懂有史以来精彩的资本运作实例,找到价值投资与公司治理之路
1966 年,比尔·斯伦斯基(Bill Shlensky)终于忍无可忍。作为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股东,在过去十多年里,他一直忍受着这家公司持续的亏损和疲软的同业竞争力。这曾是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历史接近百年,一度是整个芝加哥的骄傲。然而在过去30 年间,年轻的竞争对手通过技术革新改变了整个产业,这家公司却仍固守着自己的象牙塔。公司董事长兼CEO 是芝加哥的商界名流,却也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坚持认为“棒球是属于白天的运动”。
斯伦斯基14 岁时,父亲送给了他一份残酷的礼物——两股芝加哥小熊队的股份。自那以后,斯伦斯基不仅当了一辈子的失落球迷,还尝尽了公司治理的苦涩。在他获得股份后的14 年里,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排名中,小熊队从未进入积分榜的上半区。
事实上,14 年中有7 年他们不是垫底就是倒数第二,只有一个赛季胜率超过五成。比战绩更糟糕的是,小熊队多年未录得经营利润。
到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近60% 的比赛都在夜间举行。灯光下看比赛已在球迷中蔚然成风,大部分球队都会把几乎所有非节假日比赛安排在傍晚之后。小熊队是唯一的例外。
1965 年,城南的芝加哥白袜队平日的晚场比赛每场大约能吸引19 809 名球迷,但小熊队的平日比赛因为安排在白天,场均上座人数只有可怜的4 770 人。两队周末的比赛倒是旗鼓相当,都能吸引接近15 000名球迷。可和白袜队平日的晚场比赛相比,这个数字依然略显苍白。
斯伦斯基认为小熊队陷入了恶性循环:他们拒绝举办夜场比赛,导致上座量持续走低,球票收入惨淡,进而影响他们聘请和培养人才的能力,致使球队战绩一路下滑,球迷更不愿意来看比赛,球票卖得更差……他决定做些什么。
股东积极主义运作方式,股东干预公司治理的8 个经典案例
这是一部关于股东积极主义的作品。所谓股东积极主义,是说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愚蠢的看客。多数投资者认为,持有大型企业的股票只是一种被动跟随的投资策略。如果对公司的管理不满意,他们能做的只有迅速抛售。但有些投资者会选择积极介入,以期提升自己所持股票的价值。本书的焦点,正是股东从被动观察者转为积极行动者,并拿起笔为自身权益积极抗辩的戏剧性时刻。
股东积极主义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从上市公司出现那天起,投资人、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已经存在。400 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愤怒的股东,为了获得更多权利,开展游说活动,同时强烈谴责董事会成员假公济私的行为。19 世纪的美国,桥梁、隧道、码头、铁路和银行等上市公司股东密切关注着自家公司。特别是铁路领域,公司的控制权争夺战更是层出不穷,最激烈的当属19 世纪60年代末的“伊利铁路大战”(Erie War)。
过去一个世纪堪称美国公司监督史上的“动荡百年”,管理团队和股东之间的权力斗争频发,股东权力也逐渐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天,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能大到股东无法与之抗衡。如果不能把握公司的投票权,每一位CEO 和董事都是股东夺权的潜在对象。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股东们何以在公司控制权之争中节节胜利?哪些关键人物开启了这个被称为“股东至上”的时期?要搞清楚股东崛起的原因,我建议追本溯源,看看那些有史以来伟大的投资人当初为参与上市公司管理撰写的信件。这些信件及其背后的故事是20 世纪股东积极主义发展史的注脚。
从20 世纪20 年代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与北方管道公司的抗争,到20 世纪80 年代罗斯·佩罗(Ross Perot)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对决,再到今天广受媒体赞誉的年轻对冲基金的“英勇鼓动行为”。我们会看到代理权劝诱人、集团企业首脑以及企业狙击手,还会看到大型上市公司如何对付这些人。我从历史中选择了股东干预公司管理的8 个重要案例,并附上了股东当时写给公司管理层的信件:
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北方管道公司
本杰明·格雷厄姆写给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的信
1927 年6 月28 日
这是由职业基金经理主导的、早期股东积极主义案例之一,本杰明·格雷厄姆试图说服北方管道公司向股东发放过剩的账面现金。
罗伯特·扬(Robert R.Young)和纽约中央铁路
罗伯特·扬写给纽约中央铁路股东们的信
1954 年4 月8 日
代理权劝诱人罗伯特· 扬在1954 年向威廉· 怀特(William White)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宣战,《巴伦周刊》(Barron’s)将这一年称为“代理权争夺大战之年”(The year of battle by proxy)。
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和美国运通公司
沃伦·巴菲特写给运通公司董事长兼CEO 霍华德·克拉克(Howard Clark)的信
1964 年6 月16 日
“色拉油大骗局”(The Great Salad Oil Swindle)险些拖垮美国运通公司,同时也在公司股东内部引发内讧。沃伦·巴菲特在美国运通公司的投资是其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卡尔·伊坎(Carl Icahn)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
卡尔·伊坎写给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兼CEO 威廉·杜斯(William Douce)的信
1985 年2 月4 日
在经历了吉姆·林恩(Jim Ling)、哈罗德·西蒙斯(Harold Simmons)和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的短暂插曲之后,我们进入了以恶意收购为目的的企业狙击手时代,且看接受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Milken)资助的伊坎如何向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发起正面进攻。
罗斯·佩罗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罗斯·佩罗写给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CEO 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的信
1985 年10 月23 日
当通用汽车公司抛出巨款试图将其大股东,同时也是全世界伟大的商人之一赶出董事会时,被毒丸计划(Poison Pills)和绿票讹诈(Green Mail)挤压到极限的机构投资者再也坐不住了。
卡拉·谢勒(Karla Scherer)和谢勒公司
卡拉·谢勒写给谢勒公司股东们的信
1988 年8 月4 日
谢勒公司的大股东受到根基深厚的CEO 和对CEO 唯命是从的董事会联合掣肘,而该股东恰巧是CEO 的太太和公司创始人的女儿。
丹尼尔·洛布(Daniel Loeb)和美国星辰公司
丹尼尔·洛布写给星辰公司董事长兼CEO 埃里克·西文(Irik Sevin)的信
2005 年2 月14 日
面对绩效平平的CEO,丹尼尔·洛布主导并发起了一场正大光明的攻击。随着对冲基金业的逐渐成熟,洛布和他的支持者们从令人讨厌的牛虻摇身一变成了丛林之王。
卡洛·坎奈尔(J.Carlo Cannell)、约翰·列文(John A.Levin)和BKF 资本集团
卡洛·坎奈尔写给BKF 资本集团董事会的信
2005 年6 月1 日
董事长兼CEO 约翰·列文写给BKF 资本集团股东们的信
2005 年6 月16 日
几位眼光独到、拿着高薪的对冲基金经理对BKF 资本集团发起了攻击,指责集团为自己的对冲基金经理支付了过高的薪水。对抗的结果是留下了一片焦土,股东价值几乎被破坏殆尽。
这些案例诠释了股东积极主义的运作方式,也阐明了维权股东与公司管理层针锋相对的历史渊源。其中几个案例是股东积极行动的典型,比如恶意收购或者代理权劝诱。其他几个案例聚焦于格雷厄姆和洛布这样的创新者,他们找到了与公司管理层交战的新技巧和新方法。当然,还有巴菲特和佩罗这样的人,他们凭个人魅力改变周围的市场。
通过研究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将看到如今的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有多么大,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在未来会引发哪些问题。我们也会了解董事会的运作模式、管理团队的绩效驱动要素,以及企业监督为何如此可怕。大家此前可能无法想象,当今这个公司化的世界把多么大的责任压到了公司管理层以及股东们的肩上。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限责任型公司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世界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则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这些大型机构。正如罗斯·佩罗在一次演讲中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们所说的那样:
我们正视美国商界的一个特殊发展过程:在企业主没有绝对控股权的成熟企业里,管理层实际上已别无选择,只能让股东利益的代表人进入董事会。
就在发表那次演讲后不久,罗斯·佩罗选择离开通用汽车公司,把他心爱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留给通用汽车公司全权掌管。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佩罗一人因上市公司管理问题备受困扰。
在《滚雪球》(The Snowball)一书中,艾丽丝·施罗德(AliceSchroeder)写道:
巴菲特认为,在董事会任职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错误。
当全世界乐观、精力充沛的两位商业领袖巴菲特和佩罗在董事会拿到足够多的票数时,他们想的竟然是“让这一切见鬼去吧”。
如果说巴菲特和佩罗都需要经过一番抗争才能对董事会施加积极影响,我们这些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对大型上市公司进行有效监督呢?
佩罗离开通用汽车看起来是上市公司治理的至暗时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其实是一个救赎时刻。当眼见通用汽车豪掷7.5 亿美元,只为摆脱董事会中积极且投入的维权者时,畏缩数十年的股东们终于不再逃避,开始着眼于他们原本就该做的事。
在维护股东权利的表象下,代理权发起者更多谋求私利
从许多方面来看,股东积极主义的历史都围绕着被动投资人展开,也就是那些握有美国大公司大部分投票权的幕后群体。1914 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开始在华尔街打拼时,除了大型铁路公司,典型的上市公司都被持有公司大部分股票的少数内部人士控制。到20 世纪50 年代,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开始被新一代投资人蚕食,这些投资人非常分散,但他们都热切地希望参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大潮。代理权劝诱人从这种变化中嗅到了机会,开始在市场上大肆收购待售股票,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行动说服股东们把他们选进公司董事会。
20 世纪50 年代,代理权劝诱人运动达到顶峰,股票所有权的分散化程度也不断加剧。随后,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投票权再次集中起来。但这一次,投票权并非聚集到了企业家手里,而是被大型的专业投资机构所掌握,比如管理着大量投资人资金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到20 世纪60 年代,机构投资人堪称市场的主宰;70 年代,他们仍有相当的控制权;但到了80 年代,在企业狙击手和根基深厚的经理人之间的斗争中,机构投资人成了被收割的韭菜。目前,他们正悄悄地跟激进的对冲基金经理合作,以期牢牢把控上市公司的管理团队。
股东积极主义的实践者们履历各异,其中很多人的职业生涯起点并不是华尔街。但他们都怀抱着远大理想,而且都找到了以上市公司为目标的营利方式。从本质上说,卡尔·伊坎、罗伯特·扬、哈罗德·西蒙斯、路易斯·沃尔森(Louis Wolfson)和丹尼尔·洛布都是一类人。在“维护股东权利”的表象和个人的传奇光环下,他们都是谋求私人利益的市场参与者。
除了巴菲特之外,本书中出现的这些投资者都没有带来太多根本性改变。他们的手段或许有所不同,但也仅是因为他们面临的诸如融资渠道、企业的法律抗辩、政府的监管规定、所有者结构等动态环境不同而已。当然,重要的动态环境还是其他股东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