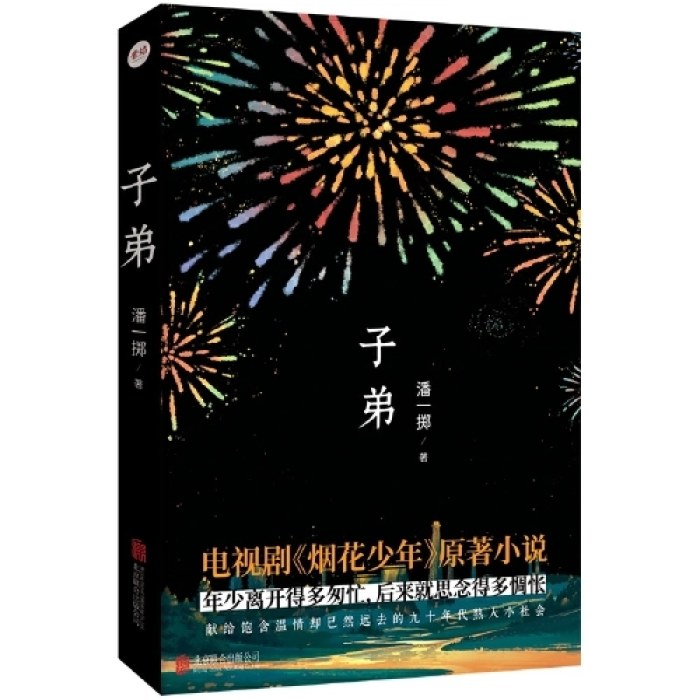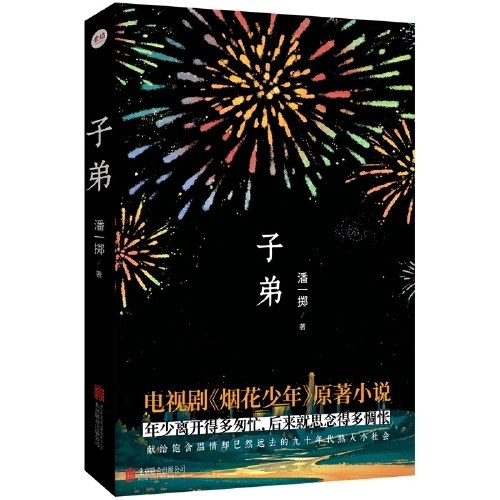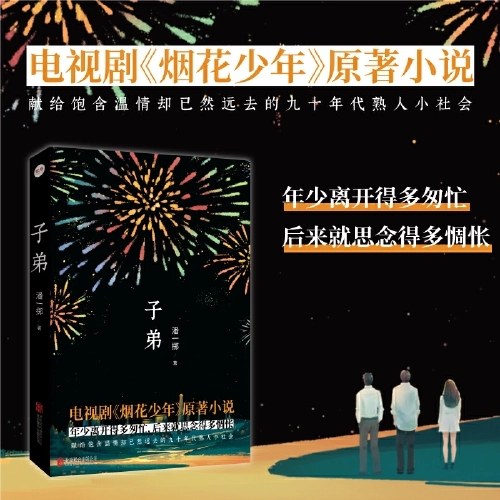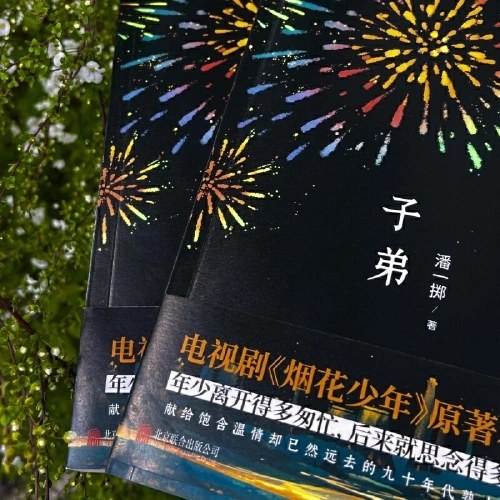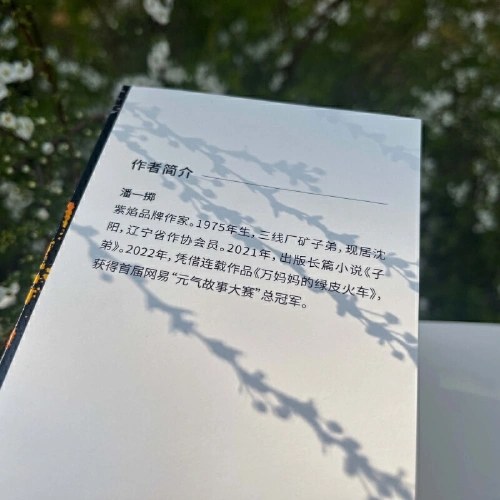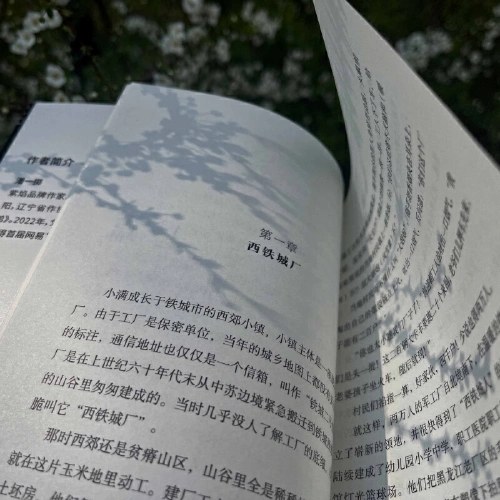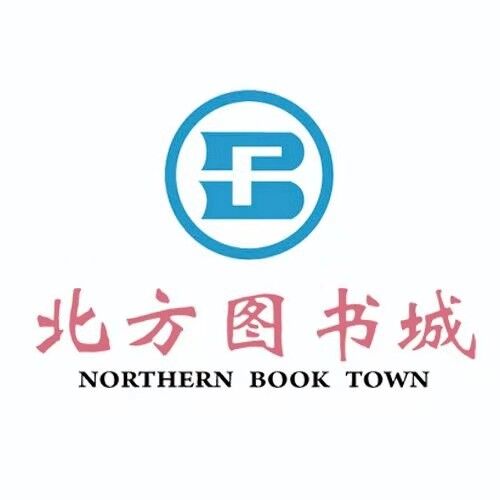在这个快速变迁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在失去故乡。或是眼看故乡日新月异,不再是童年的模样;或是在外漂泊多年,忘记了乡音,也被故乡所遗忘。
男孩小满的故乡是一座工厂。商店、医院、学校、家属院围绕工厂拔地而起,仿若繁华的小上海;既是同事又是老友的邻里关系,汇成饱含温情的熟人小社会。大院里的八卦新闻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放学后的爱情总逃不过大人的眼睛。早恋的小满难逃厄运,只能守在女孩窗前,想多听一听她的声音。
当他的青春与爱情挥洒殆尽,工厂也在经济转型中走向衰败。下岗、打工等不安的词语涌入安稳的生活,带来瓦解和漂泊。曾经熟悉的一切渐渐消失不见,故乡轰然倒塌。
小满这才明白,原来最可怕的不是开始怀念,而是无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