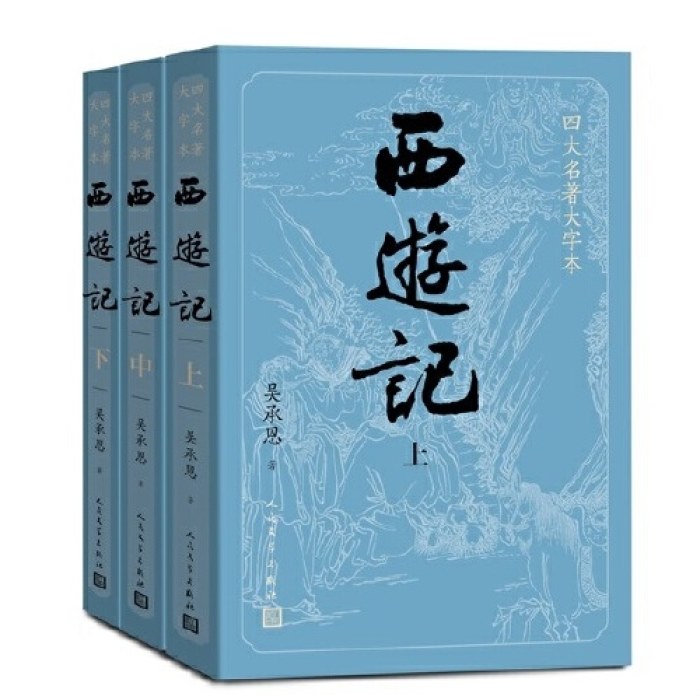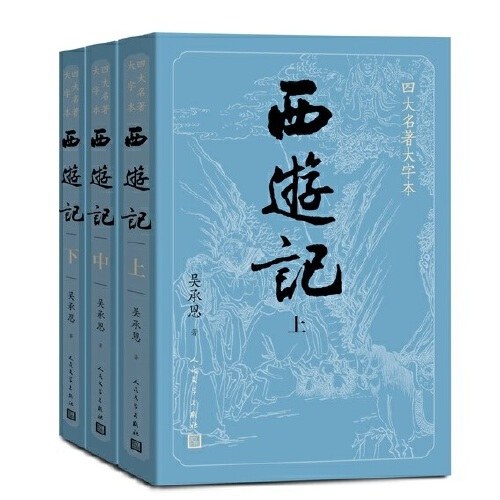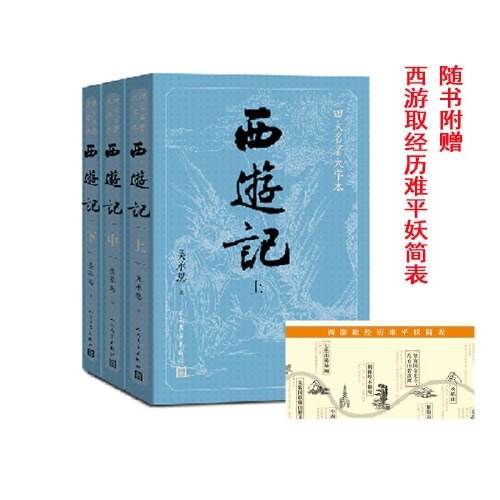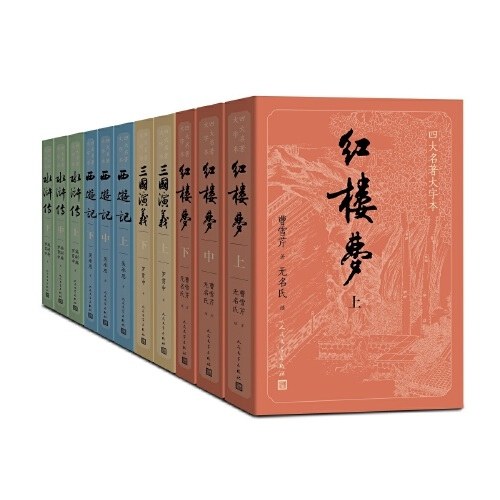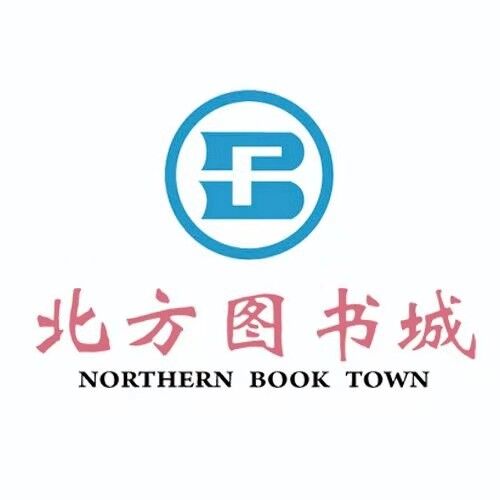前言
一
《西游记》约成书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明代中叶,它和比它先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后来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是我国明清时期有代表性、著名的长篇小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光辉成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
《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有它自己的特点,读这部小说,有几点是必须理解的。
,《西游记》跟一般古代小说不同,它是一部具有神话、童话性质特点的小说。
同志在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时,曾经指出:“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矛盾论》,《选集》卷。同志在这里指出了神话或童话这类文艺创作具体的性质和特点,这对我们认识、理解《西游记》这部小说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家知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三卷。神话以及神话小说《西游记》这类作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也同样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它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已。《水浒传》、《红楼梦》里面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品里展现的矛盾斗争,除少量属于宗教迷信或文学幻想以外,一般地说,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当然作品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西游记》里面所描写的孙悟空、猪八戒、玉皇大帝、神仙妖魔,以及孙悟空闹天宫、闯地府、闯龙宫、智斗二郎神、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故事情节,则是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西游记》里面写到的那许多出自文学幻想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仍然离不开现实,它们是以作者对社会现实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理解作为创作的基础的。
《西游记》写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人物的神通变化,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一个人怎么能够飞天钻地,呼风唤雨,变这变那,甚至能变一座土地庙儿呢?一个筋斗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远,那支金箍棒幌一幌就碗口粗细、数丈长,可是一变又会变得小如绣花针可以放在耳朵里,这是可能的吗?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很喜欢这个活泼、机智、乐观,富有斗争精神和无穷本领的人物,连同他那支神奇多变、威力无比的千钧棒。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孙悟空闹天宫、斗妖魔,这些幻想的形式中包含有我们能够理解的现实的内容,具有某种社会批判的意义,而且这些浪漫主义的描写在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里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读《西游记》时,必须记住它是一部神话小说这样的性质特点,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这部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意义。过去悟一子、悟元子之流穿凿附会地把《西游记》说成是“谈禅”(谈论佛理)“释道”(阐释道教)的书悟一子陈士斌撰《西游记真诠》、悟元子刘一明撰《西游记原旨》,均用佛道思想解释《西游记》的真意。如刘一明在《西游记原旨·读法》中就说《西游记》是“神仙之书”,“乃古今丹经中部奇书”,在《西游记原旨序》中又说,读《西游记》的人,“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这些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说法。,后来胡适又把此书说成是“玩世主义”胡适《西游记考证》说:“这七回(引者按:指《西游记》前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他歪曲、抹煞了整部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这跟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分不开的。,这些都是歪曲、抹煞作品社会内容和意义的错误的评论。
第二,《西游记》跟那些由作家个人创作完成的小说不同,它是古代民众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成果。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跟《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由作家个人写成的情况不同,跟《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有类似之处,其故事都是经过长期的流传和许多人的记述或创作,后由一位作家作了总结性的再创作而后写定的。
唐僧取经本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僧人陈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印度)取经。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前后花了十七年时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终于取得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到长安。回国以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佛教遗迹兼及土地出产、风俗人情等状况。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彦胔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他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虽写真人真事,但因前者是写佛教发源地的见闻,后者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的色彩,《西域记》里面更是记述了许多宗教传闻和佛经里面的故事。又由于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唐僧竟能孤身西行、远涉异域,终得取经东还,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有某种传奇性。这样,唐僧取经故事流传到了民间,就逐渐离开了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的内容。
到了宋代,关于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说话人甚至已把它作为说话的专题。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南宋时候说话人使用的话本。它已经不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样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写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降妖伏怪的故事。这个话本故事情节很粗略,艺术想象力和文字比起吴承恩的《西游记》来差得很远。但它首先把取经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又开始把故事的主角由玄奘转为猴行者。书里的猴行者和深沙神,显然就是后来《西游记》里孙悟空和沙和尚这两个形象的前身;猪八戒这个形象则还没有出现。
到了元代,西游取经故事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推断,元代至明代初年已经有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小说。可惜我们已见不到当时《西游记》话本的全貌,只在明代永乐年间(公元一四○三至一四二四年)编纂的《永乐大典》里面,发现有一段题为“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文字,约一千二百多字,所引书籍题为《西游记》。这段文字相当于现在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和第十回的前半部分。《永乐大典》三一三九卷保存的那段话本残文,跟吴承恩《西游记》第九、第十回,都写了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故事。除了话本《西游记》里面两个渔翁,在吴本《西游记》里面改为一个渔翁、一个樵子,并且增加了一大段渔樵两人诗词对答之外,两者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卜者袁守诚算定下雨“三尺三寸四十八点”,两书记述也都一样。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吴承恩创作时,曾经参考过《永乐大典》所引到的那部《西游记》话本。此外,在一部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曾多次引用到一部题为《唐三藏西游记》的平话。虽然《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有关文字并不是那部话本的原文,而是经过转述者简化过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那部话本已经写到了有关的许多故事。
西游取经故事很早就在舞台搬演。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均已失传。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还在。这个剧本有唐僧出世的故事,没有魏征梦斩泾河龙和太宗入冥的故事。孙悟空是此剧的主角,但“神通”远不如后来《西游记》所写的那样,整个形象跟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的形象有本质的区别。
自唐代玄奘取经的历史事件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这些书籍出现以后,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关于取经故事的民间口头传说以及话本小说和杂剧,使西游取经故事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文艺形式得到不断的发展。在长期的故事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不断地改造和丰富原有故事的情节内容,同时也把他们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对于封建社会里种种丑恶势力的批判和斗争,乃至他们征服自然力的理想和愿望注入了取经故事。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仅直接继承了有关取经故事的民间文学的题材,而且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使这部神话小说在生动有趣的艺术描写中常闪烁出可贵的思想光彩。譬如小说第四十五回孙悟空对着一群司雷电风雨之神发号施令:“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充分写出了孙悟空在自然之神面前的雄伟气魄和强大威力。这些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民驾驭自然的热烈愿望和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这是古代人民“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表现。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可以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民间文学,就没有吴承恩的《西游记》。当然,前者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东西,在过去这个基础上来一个集大成的再创作,写出一部规模更加巨大、艺术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的古代神话小说,这就是作家吴承恩的贡献了。
第三,吴承恩讽刺、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只是幻想有所改良,并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制度。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他生活在明代中叶,约当公元一五○○年至一五八二年间;出生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僚而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祖父“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亲“卖采缕文鄃”(卖彩线和绉纱一类的丝织品),是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他极好读书,常遭官府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作者在文中说:他的曾祖父做过“馀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亲是个店肆主人,极好读书,“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据《射阳先生存稿》卷三,故宫博物院本。
……